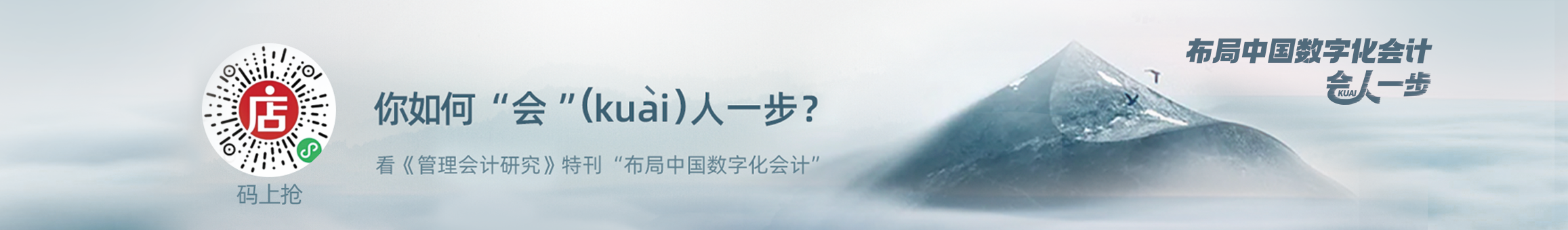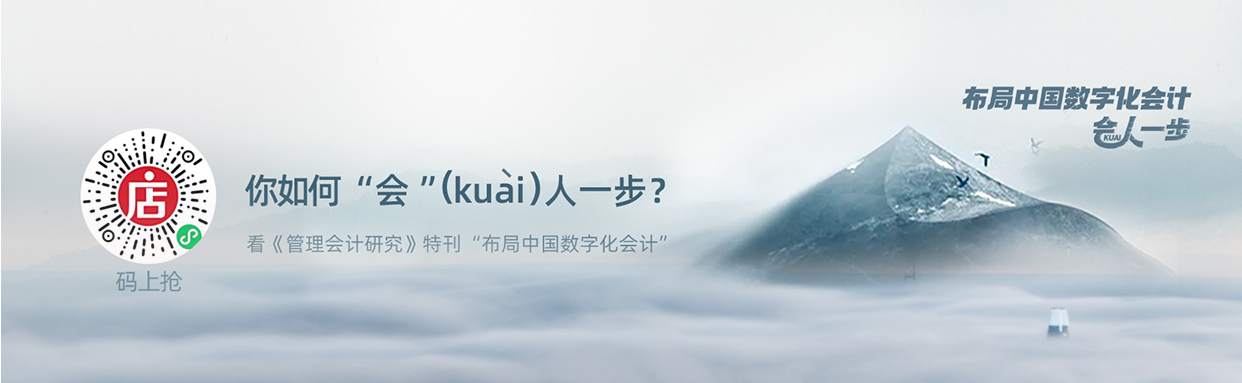外源式引进、技术垄断与关键基础产业延误 ——基于盐湖股份引进制镁设备的案例研究
一、引言
关键基础领域技术不足是中国面临的重要现实问题,在新发展阶段3尤为突出(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课题组,2024)。在新发展阶段,中国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不断缩小,国际市场竞争环境日趋复杂,守成大国对中国技术领域的封锁不断加剧(王一鸣,2020)。2021年,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部、财政部、商务部、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六部门发布《关于加快培育发展制造业优质企业的指导意见》,提出加大基础零部件、基础电子元器件、基础软件、基础材料、基础工艺等领域关键核心技术、产品、装备攻关和示范应用,肯定了关键基础产业技术进步的重要作用。金属镁工业是典型的关键基础产业。作为人类目前掌握的最轻的金属结构材料,金属镁被广泛用于航天航空、国防军工等基础领域,在2020—2022年相继被美国、欧洲、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列为关键原材料(王安建 等,2022)。中国制镁技术短板使得生产过程污染严重且产品纯度不足,难以向高端产业迈进(李鹏业 等,2017)。向西方国家购买高纯度金属镁需要办理出口许可文件并签订用户非军工声明协议,在高端镁获取方面受制于人(李芳 等,2020)。因此,金属镁工业实现技术进步对打破国外技术垄断、助力航天航空等基础产业做优做强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外源式技术引进是指我国在开放条件下引进来源于国外的技术,主要包括以国际技术贸易为主的直接技术进口和通过外商直接投资(FDI)、进口贸易等渠道以技术外溢为特征的间接技术引进(龙少波 等,2022),是中国自成立初期直至“十二五”时期摆脱技术缺失困境的重要手段(王丹莉,2019)。按后发优势理论(Awate et al.,2015)理解,外源式引进规避了长周期高风险的自主研发,有助于后发经济体快速实现技术进步。然而,国际经济格局的加速调整使得守成大国加强了技术领域的垄断措施,尤其对于关键基础产业(王一鸣,2020)。现有研究也发现,引进关键设备并不能有助于企业创新,反而会对企业的资产价值和生产效率造成负面影响(王钰涵 等,2023)。基于比较优势理论(Dollar,1993),技术差距作为技术领先主体的比较优势,是其维持市场竞争优势的关键要素(林毅夫 等,2003)。根据资本边际报酬递减规律,新兴经济体往往技术进步速度更快(袁建新 等,2010)。因此,技术输出方必然不愿失去技术优势,更希望垄断自身技术。中国虽然在部分终端产品方面已经形成较强的竞争力,但在基础材料等领域普遍存在技术短板。在新发展阶段,市场竞争加剧(廖慧文 等,2025),外源式引进能否继续作为关键基础产业实现技术进步的主要手段,是关乎中国实现价值链攀升、维护产业链安全的时代之问。
基于此,本文以国内首次尝试全盘引进电解法制镁技术的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盐湖股份”)为案例研究对象,基于比较优势理论从博弈竞争的角度直观具象地回答新发展阶段关键基础领域是否适宜通过外源式引进实现技术进步的重要现实问题。盐湖股份举债从挪威等多国引进制镁设备并建设镁板块综合利用项目,欲打造“世界上最大的镁基地”,而镁板块综合利用项目建设耗时近11年,预算数额不断增长,最终减值冲毁,镁业务也由于无力偿债随即被剥离。分析盐湖股份的分部收入发现,盐湖股份始终未生产销售镁产品。从企业研发情况看,外源式引进未引入实质技术,也未能与企业现有资源发挥互补作用。从生产角度看,引入的设备与盐湖股份现有环境条件不适配,且设备本身存在故障缺陷,技术瓶颈的存在导致无法产出,基于路径依赖持续追加投资仍然无果。分析外部主体的动机和博弈竞争格局发现,进入新发展阶段,中国在经济、科技等领域的迅速崛起使其与先发主体的竞争更为激烈,原有博弈竞争均衡发生转变,外部主体不愿失去技术比较优势的动机使其更不愿进行技术输出。进一步分析发现,外源式引进失败延误了基础资源利用和基础领域做大做强的进程。可见,在实践层面,仅依靠外源式引进在新发展阶段已不再可靠,实现基础领域技术突破还应更多地实施自主研发。
本文可能的贡献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本文从博弈竞争的角度丰富了新发展阶段中国实现技术进步的策略研究。现有文献主要集中于从结果层面对外源式引进展开整体讨论(Zhang,2012),而较少基于各主体比较优势对其动机选择进行情景式分析。本文聚焦关键基础产业,基于比较优势理论阐述了新发展阶段经济体间博弈竞争均衡的转变,为回答关键基础产业如何更好地实现技术进步进而提升国际竞争力的时代之问提供启示。
第二,本文对外源式引进后果的研究形成有益补充,同时识别出制约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延误关键基础领域进步的重要因素。一方面,现有研究考察了技术引进对企业生产率(Zhang, 2012)、经济增长(袁建新 等,2010)等方面的影响,而尚未从产业长远发展、竞争优势获取的宏观角度进行充分讨论。本文发现,外源式引进失败可能带来延误发展机遇的负面后果,为监管部门重视和关注大规模引进提供政策启示。另一方面,承担关键基础产业发展使命的国有企业长期面临“大而不强”和低效率问题,不仅由于受到代理问题和政策性负担的挑战,本文发现外部主体的技术垄断同样是制约国有企业发展的重要原因,为推动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路径启发。
第三,本文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理论和现实证据。一方面,与以往研究认为外源式引进更为快捷适用(Awate et al.,2015)、应当发挥后发优势多引进成熟的技术不完全相同,本文分析发现,新发展阶段博弈竞争均衡改变,外源式引进已难以推动技术进步,有助于加深对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理解。另一方面,新质生产力是由科技创新主导的高效能生产力,其产生的基础在于技术突破与进步(周文 等,2023)。本文为实现生产力跃升质变、筑牢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根基提供借鉴。
本文摘自《管理会计研究》2025年第4期,购买纸质刊请点击本链接至微店购买
......